币安交易所 Binance jiaoyisuo 分类>>
Binance 币安 ——比特币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2025当科幻照进现实我们如何在加速的时代里自处?
加密货币交易所,币安钱包,币安app官网下载,币安电脑PC版,币安交易所网址,币安app下载,币安邀请码返佣,币安交易所官方网站下载,币安交易所,币安,币安下载,币安注册,币安交易所网址,币安靠谱吗

:我们高中是寄宿制,没有家长管着,终于可以阅读所谓“闲书”了。那段时间就大量阅读了科普类和文学类的作品,它们从不同方面为我揭示了世界的复杂。所以在刚开始创作小说时,我很自然地会同时从这两方面入手。投稿的第一篇小说算是青春文学,发表在《萌芽》,第二篇就发表在《科幻世界》。对我个人而言,这两类创作之间其实没有本质区别——但我后来发现它们的读者群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,比如《萌芽》的读者是女孩子偏多一些,《科幻世界》的读者是男孩子偏多。
王侃瑜:我感觉也是。越来越多传统文学的作者开始关注和创作科幻了,但似乎面向的受众很不一样。因为我同时也在做中国科幻的海外推广工作嘛,编选过一些英文选集,也负责落实一个翻译专栏,沈大成的作品就被选入过我们的科幻选集、科幻专栏,还入围过科幻奖项。我发现国外的类型边界可能相对没那么明显,一是科幻与奇幻或者其他推想文学类型之间的边界模糊,二是推想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分野不大。国内的分类好像相对比较明显,哪怕最近几年多有跨界融合,但这个“界”本身还是存在的。
王侃瑜:是啊!技术路径、审美倾向、读者市场的区别,但本质上都是小说。我印象中,科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受主流纯文学期刊认可的,可能只有童恩正、叶永烈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过科幻,再后来就是刘慈欣破圈受到文学界和评论界关注,那已经是2010年以后了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主流文学期刊都开始做科幻小辑、科幻专栏,释放出更明显的欢迎信号。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?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花城》等期刊发表的科幻和《科幻世界》《科幻立方》《银河边缘》发表的科幻又有哪些差异?
前阵子正好看到科幻作家杨枫那篇总结《龙与瓷砖虫:2024年本土科幻中短篇小说概览》,他提到在过去一年里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等头部文学期刊都在发表科幻作品,《边疆文学》《文学港》《文艺报》还设立了固定的科幻专栏,全年共计发表了超150篇科幻作品,其数量已经超过核心科幻刊物(《科幻世界》《科幻立方》杂志)的128篇了。我自己的科幻小说也有很多是发表在纯文学刊物上面,但我也有些失落地意识到,其实大部分科幻读者是不会专门去看纯文学刊物上面的科幻小说的。而那些发表在《科幻世界》上面的作品,则会被更多人讨论、评价。
王侃瑜:是诶,感觉这是审美趋向不同带来的很大误解。科幻读者确实不会去看纯文学杂志上的科幻小说,所以很多科幻迷并不是因为我的科幻小说而认识我,反倒是因为科幻活动组织经历,国际推广工作,甚至是研究工作而认识我。其实我们去看科幻文学的奖项,也会发现审美趋向的不同。银河奖、星云奖这样从科幻社群内部成长起来的奖项,可能代表着核心科幻迷群体的审美,个人觉得科幻创意在这些作品中还是受到比较大重视的。而像贺财霖·科幻文学奖这样依托《文学港》杂志的奖项,评选出来的作品则相对更重视作品的文学性,我有听说过一些星云奖、银河奖得主在这个比赛中折戟,并觉得意外。当然,这些作品本身都是优秀的,只是突出的地方不一样,并没有孰高孰低。
修新羽:高中住校期间,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手写在本子上,等周末回家再一点点整理到电脑里。所以高中时期,也是我唯一的一段有创作“手稿”的时期。现在我们经常能在博物馆里看到某某著名作家的某某手稿。我时常会想,若干年后,我们这代人中的著名作家被拿来拍卖的会是什么?是移动硬盘吗?是他用来打字的笔记本电脑吗?我们都看过电视,用过手机,我们都用过微信,我们都网购过商品,在大的技术浪潮中,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。对技术的体验,是我们最共通的一种体验。然而,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意识到,技术发展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改变。
王侃瑜:科幻作家威廉·吉布森不是有句名言嘛,“未来已经到来,只是分布不均”。技术的发展,对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人带来的改变都是不同的、非均质化的。过去,对于“未来”的想象和定义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,通过对科技的垄断、文化产品的输出等,让大家觉得“未来”就像好莱坞大片里那样,高楼大厦、科技公司、宇宙飞船……但随着这种垄断被打破,全球南方国家纷纷开始构建和讲述自己的未来,去打破单一的、线性的、简单的未来叙事。并且我觉得这些象征未来的技术,其实在中国更加深度地嵌入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,这几年大家都很明确地有“未来已来”的感受。我在挪威生活期间,还有在欧美其他国家旅行期间,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那里的智能手机普及率远不如中国,也没有相应的一整套移动应用生态。
修新羽:因为之前在“科技+零售”公司工作过,我对这方面思考得比较多,也举几个例子吧。前阵子京东美团大战,大家现在对“即时零售”“30分钟外卖到家”都已经很习惯了。这种生活的“便捷性”或许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对生活的态度,当我们想吃什么立即就可以吃到,我们控制欲望、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否会被削弱?当我们开始共享自行车,共享充电宝,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在享受更大的自由?当现实变得如此快速、复杂、技术化,以至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难以捕捉其本质的“不可思议性”时,科幻其实提供了一种更贴切的“模型”来理解和仿真这种现实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科幻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未来的幻想,而是关于当下超真实体验的隐喻。
王侃瑜:顺着你这点讲下去,学者朱瑞瑛就认为科幻和现实主义并非彼此的对立面,而是一个光谱的两段,科幻其实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。科幻小说以一种高密度的“摹仿”来再现现实,只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很多现实能量层级过高,很难以直接的方式来进行呈现,所以科幻小说成了一种比较合适的表达形式。科幻的语言系统将所有隐喻、象征、诗性的事物都当作“真实”的事物来处理,由此进入到更深的写实层面中去,便于处理一些像人工智能、气候变化之类的议题。
王侃瑜:十几年前,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那时候大家对科幻的认识不够,觉得只是开脑洞甚至怪力乱神,产生了很多误解。我以前参加《萌芽》和《联合文学》举办的两岸文学营,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青年写作者在一起讨论文学,我说我是写科幻的,好像就有点让人吃惊,但后来有台湾地区的青年作家跑来私下和我说,其实他们也很喜欢看科幻、奇幻,只是在文学的场合下谈这些似乎上不了台面,哪怕有写怪物小说的也顶多是往民俗、传说那方面靠。
修新羽:当时《三体》还没有火出圈,大家下意识会觉得科幻是“点子文学”,是虚张声势的花架子,觉得阅读一篇科幻就像看一场魔术表演,翻过扑克就有鸽子从里面飞出来,缺乏对人性的挖掘。我在文学期刊当编辑的时候甚至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在接到有科幻元素的投稿后去跟作者沟通,看能否收录进科幻小辑,投稿者连忙否认,说自己写的不是科幻,只是有点儿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风格。而很多不太阅读纯文学作品的人也会认为,纯文学是门槛很高、风格化很强的艺术作品,是佶屈聱牙或者枯燥无聊的。其实纯文学的审美千差万别,有些作者会更照顾读者的感受,有些作者喜欢挑战读者,或者说,至少是不“讨好”读者,在叙述上增加许多难度。由此可见,虽然科幻和纯文学正在逐步互相了解,但目前的了解程度确实不够,经常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去想象对方。
王侃瑜:科幻文学也是如此,但感觉目前主流的科幻审美还是会倾向于照顾读者。刘慈欣就说过他的创作是“外圆内方”的,“外圆”是说表现形式上会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感受,根据情况进行变通;“内方”是说他想表达的内核是不变的。有时候科幻杂志上出现堆砌意象和公式的作品,很容易受到大范围批评,科幻读者好像不太认可这种为了风格化而风格化的写作方式。但韩松是个例外,他的个人风格实在是太强烈了,所以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,无感的人也就彻底无感。有科幻机构把韩松和刘慈欣总结为“中国科幻的两极”,有两极就可以有很多极,无论软硬,无论偏向技术还是偏向哲思,无论是情节见长还是文字见长,我感觉当大家都愿意接受不同的风格都可以是好的科幻时,这个文类可能是在健康发展的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,当科幻有许多不同风格时,其核心魅力可能就被稀释了。
还是讲点儿个人经历,有次我给科幻杂志投稿,收到的退稿意见是:“有设定也有故事,但是过于追求叙事方式和技巧,反而将设定的新奇感冲淡了,缺失了通俗小说的那种通俗感,更像纯文学作品了。”当然,也有可能主要是故事性不足,编辑为了退稿不尴尬才勉强夸了夸。但这个退稿意见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。我想到了小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,一个雕塑家完成作品后,找他的朋友来看,他的每个朋友都说,你这个雕塑的手雕得真好,栩栩如生。他听了勃然大怒,干脆把那双手砍掉了,因为他觉得手已经喧宾夺主了,让人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作品了。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,很多读者在阅读科幻的时候,很关注作品的可读性,也享受由技术推想而展现出的奇观。或许,无论是纯文学或者科幻,每一个作品都要寻找对它而言最合适的尺度。
王侃瑜:这可能也是写作或者艺术创作中最神奇和微妙的地方,没法用一个公式或者客观标准去量化这个尺度。有时候读一篇作品,哪儿哪儿都挺好的,没什么大问题,但就是感觉不太对劲。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会有很多废稿,所以写得很慢,有时候也觉得是这个尺度不太对,只能推翻重来或者反复去调整,呈现出一个最终让自己满意的效果。写多了以后,我开始学会区分自己不同的作品脉络,每个脉络下的书写主题和风格也不尽相同,对应的尺度也不一样。有些篇目里的科幻元素很弱,比如《海鲜饭店》和《冬日花园》,更重在一种氛围感的营造和主角心境的刻画上,我自己将之称为“散文式的科幻”,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来自纯文学界的反馈。有些篇目里的科幻设定和技术细节比例就比较高,比如《火星上的祝融》和《岛与人》,这类作品好像科幻界的反馈就会更多。
王侃瑜:是的。我们几位获奖者一起坐在华师大的校园里,和DeepSeek合作进行人机共创。考虑到现场创作时间有限,我平时写得又很慢,我就想索性把创作的自由交给AI吧。我提供了基础的科幻设定和哲学思考,并给出提示内容引导AI进行创作,根据其生成内容进一步进行追问和调整。最终呈现出来的文字内容超过90%都由AI写作,略加人工删改和润色,但其实还是不大能看。我和其他作者的感受是一样的,AI目前在文学创作上的能力还很有限,要修改AI的创作内容比自己写还费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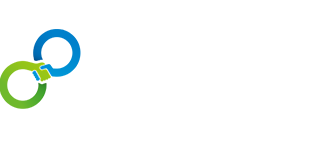
 2025-07-23 07:49:33
2025-07-23 07:49:33 浏览次数: 次
浏览次数: 次 返回列表
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





